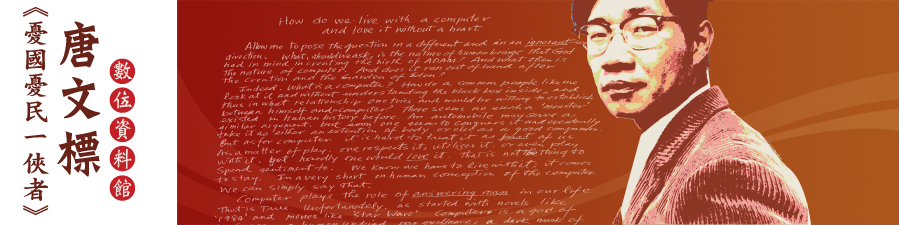台灣現代文學的捍衛者:發現張愛玲的唐文標
- 座談日期:99年 1月8日
-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A202室
- 主持人:陳萬益教授
- 與談人:尉天驄教授、周芬伶教授、莊宜文教授
張愛玲資料彙編與整理(尉天驄教授座談內容擷取)
所以他讀張愛玲的小說,讀得非常喜歡。他也研究四○年代的文學,不但喜歡張愛玲,也喜歡蘇青,說他的文筆好,但是他也有幾個問題,例如說在上海租借地的生活是看到希望的,張愛玲的生命也讓人看不到「希望」。他非常浪漫,為了認識張愛玲,他就委託香港最好的朋友進入大陸,花了很多錢,把張愛玲所有資料都買出來了。(現在容我介紹 這一位在座的老兄,老關!你們不要搞錯,不是批評現代詩的關傑明。)唐文標覺得,在張愛玲的書寫裡找不到路-張愛玲是李鴻章的曾外孫女,父親那麼有地位,生在那一時代如此的一名女性,她一生愛情也沒有了,一生的交往都沒有正常-唐文標長得不好看,倒非常憐香惜玉,所以他寫了「一步一步走到沒有光的地方」,張愛玲是這麼一個人,他這樣做,外面就有人犯小心眼,說唐文標想利用張愛玲發財,老天啊!唐文標什麼都會,就是不會發財,我曉得唐文標那人,要騙他是太容易了。他把資料拿出來以後,就編了張愛玲資料大全,還有個張愛玲卷,一個交給皇冠,一個交給中國時報印。那時中國時報的余紀忠跟皇冠的平鑫濤正是死對頭,正好抓到,平鑫濤打電話給余紀忠,余紀忠說我告訴你,所有報社印出來的資料,我都不要了,全都送給唐文標。唐文標打電話給我,說要把這些書送到我家來,我家樓上有違章建築,有地方放書。過了一個鐘頭,書送到他台中家裡,他搬書,那時候他癌症開過刀,細胞很脆弱,搬了不到一個鐘頭,唐夫人邱守榕打電話告訴我,老唐血管破裂,送入台中榮民總醫院。
評論角度與研究方法的示範(周芬伶教授座談內容擷取)
第二點,他對張愛玲的見解很多是繼承傅雷先生的思想。最大的特點是,對作品的思想、結構的分析,比如說為什麼連環套是一個失敗的小說。他把連環套又挖出來,用各種方式討論這是個非常失敗的作品,這非常激怒張愛玲,我想張愛玲應該不怎麼喜歡唐教授,不過我想張愛玲也沒有喜歡過誰。但他是無畏地去接近她的東西,把她當年的瘡疤都挖出來,因為當時這篇作品她被罵被腰斬,他把它翻出來,之後又把傅雷的文章弄出來,這等於是在她的傷口上撒了鹽,當然她會不能接受,但我覺得他的價值也就在這裡,就是不考慮作者到底能不能接受,而是把它當成一個公案來處理。這給予我們做現代文學研究的人有非常多的幫助。
除了是一個思想的重心,另外就是很完整的一個示範方法,從年表的製作,到怎樣去把一個文學問題、文學史的公案提出來做討論。所以我們稱他是張愛玲上海文學租界的發現者,他還發現了蘇青。其實蘇青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家,我也是對這作家相當地有興趣,如果他能多活幾年的話,他對上海文學的研究會更豐富,會讓我們看到一個城市,不只是在講一個人,而是一個階段一個時期,某個城市裡面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作品。她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特色,在戰爭時期、在一個是非不明的時代,就有這樣的作品存在,對於我們不管是書寫的人或是研究者,都是非常大的啟發。
獨立評論的實踐與精神(莊宜文教授座談內容擷取)
我的觀察跟周芬伶老師也是很相近,就是我想他這些批張的文章,某方面受到傅雷的影響,比方說對陰暗的批評,然後對於張愛玲炫才的批評,或是她會用一些套語,其實是受到傅雷的影響。剛剛周芬伶老師說張愛玲很在意別人的眼光,我也是這樣認為。她會對傅雷的評價表達自己的寫作觀點,所以她寫了〈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就變成我們現在討論張愛玲作品很重要的一篇散文,或是張系國對〈色,戒〉的批評,她也特別寫文章替自己辯駁,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色,戒〉的一個很好的材料。她為什麼不理唐文標?我覺得她根本不屑於唐文標這樣的切入角度,其實張愛玲根本一直以來是不以為然的,也許她夠聰明到能夠看出唐文標對她由愛而恨的情緒。
在唐文標寫出了這些東西之後,很有趣的是,朱西甯、銀正雄他們都也寫了幫張愛玲說話的文章,銀正雄跟王翟是採取比較客觀的立場,其中一位比較走火入魔的是朱西甯,他是把胡蘭成跟張愛玲都神化了的作家,所以他寫了文章〈先覺者、後覺者、不覺者〉這篇文章也格外地苛刻,朱西甯的評論有時是非常犀利跟尖銳的,特別是當他碰到他覺得是「異端邪說」的對象的時候,而唐文標剛好就激勵了朱西甯來寫這篇文章。據我看朱西甯的文章,大約有八篇左右是談到張愛玲的,而這篇格外地深刻而犀利,因為朱西甯認為張愛玲是先覺者,是以敏銳的直覺走在時代之前的,他說胡蘭成是從張愛玲這邊獲得直觀的體悟,他又引胡蘭成的觀點,認為西方社會是物質的蛹,終會枯竭,而中國的哲學則是通過無而循環不息。所以他批駁唐文標只知道「有」的世界,不知張愛玲作品高妙處是承載了不可道的「常」。所以當他寫出來這篇文章之後,唐文標也非常地鬱悶,他在後來的回憶說,朱西甯一向是黨同伐異,他說,「可是我至今從來不懂何以張氏是先知者,朱氏是後知者,而我是不知者?」然後他覺得朱西甯這種玄而又玄的這種話,他無法理解。我想這也就反映出來,這兩位評論者,他們其實是全然不同的人生視野,以及全然不同的文學觀。
- 座談會完整影片:http://www.media.nthu.edu.tw/media/show/id/808
- 座談會記錄全文:台灣現代文學的捍衛者:發現張愛玲的唐文標(PDF)
-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