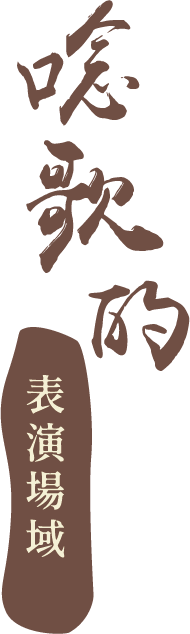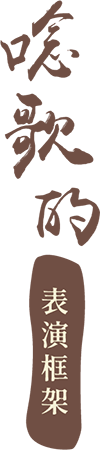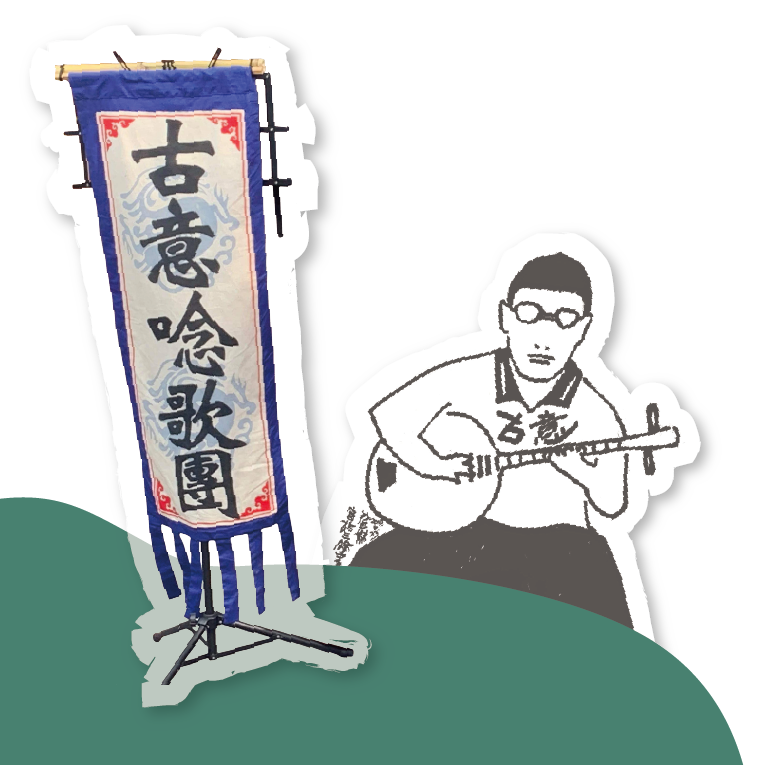「唸歌」是農業社會台灣人民的主要娛樂,源自於民間傳唱的「歌仔」,以「歌仔」唱唸著民間故事,就成為「唸歌」;而將唸歌寫成冊,便稱作「歌仔冊(簿)」;將歌仔曲調吸收入戲,是為「歌仔戲」。
「歌仔」在明末清初傳至台灣後,民間即流傳著從民歌發展成的「敘事歌」與「勸世歌」,曲調亦多採自台灣本地民間歌謠與閩南漳泉,最後成為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台灣唸歌。早期唸歌除了是民眾的娛樂,也是民間藝人走江湖的技藝。
現在,「唸歌」成為台灣的說唱藝術,常見一至二人進行表演,有時候亦可多人一起。表演時會使用月琴、大廣弦、鑼鼓等樂器伴奏。而唸歌使用的曲調有上百首,包含民間小調、南管、北管等,唸歌歌手會根據故事內容、現場氣氛,挑選合適的曲調搭配,如開場時,會先以難度較高的曲調來表現唱功,以吸引觀眾。
表演場域從「廟埕」到「電台」
唸歌是早期台灣人民的休閒活動之一,形式相當自由,常常是因情境所感或一時興起,而唱唸出平時所聽聞過的詩句。
一開始唸歌歌手是以「吟遊詩人」的身分登場的,類似今日之街頭藝人。因唸歌具表演性,能吸引大眾的注意,也因此成為商業用途的切入點。例如在廟埕或夜市中常見的「賣藥仔團」(王祿仔仙,台語。指行走江湖,以賣藥、賣藝為生的人),就是利用唸歌表演聚集人群,並在表演中間穿插「賣藥」──唸歌歌手常常會說唱到故事精采、緊張處時突然中斷,賣藥老闆趁機廣告生活常備藥品,觀眾因急著聽後續故事,往往願意掏錢購買。
根據微笑唸歌團團長儲見智的調查,當時專業唸歌歌手的收入頗為豐厚,足見唸歌表演在民間受歡迎的程度。專業唸歌歌手須經過一定的學習與訓練過程,他們雖然不以藝術家或音樂家自稱,但其傳唱過程中,對於語言文化和音樂性的嚴格要求,可以知道專業唸歌歌手其實自主負起文化使命感。
隨時代變遷,唸歌的表演場所曾一度轉入電台表演,有時仍然和賣藥的商業行為扣連。直至近期,「台灣文化」被重新重視,唸歌方才逐漸被視為珍貴的口頭傳統,成為表演藝術的一環。
唸歌方程式──歌仔頭唱到歌仔尾
唸歌表演大抵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作為開頭的「歌仔頭」,其作用是為了吸引聽眾注意力。歌仔頭的演唱內容會依據現場情境而有所變化,通常是表演者自我介紹、提起故事的梗概或關鍵人名,例如山伯英台、廖添丁等;有時會提到這首歌的用意,如勸人為善,甚至是聽歌識字、鼓吹消費行為等等;其長度平均在一葩至四葩之間,如:
總請例位眾兄台
哪欲聽歌就緊來
來喔,來聽唸歌喔(口白)
唸歌表演真精采
頭聽至尾恁就知
第二個階段即是故事內容,此階段除唱詞以外,有時會搭配口白,表演過程往往會視現場觀眾的反應,改變部分演唱內容的詞彚,以進行互動。
因為一個完整的故事演唱通常極長,難以一次完整演出,故唸歌表演在結束前會有另一段「歌仔尾」,作為暫停或結尾。歌仔尾會對故事進行總結、勸世、吉祥話祝福等,或者含有不同目的的推銷或換場說明。有時也會穿插幽默的調侃,讓觀眾會心一笑。例如:
囝仔聽歌好育飼
老歲仔聽歌呷百二
查某聽歌生後生
查甫聽歌予你娶細姨
將唸歌視覺化,獲得紅點大獎
因為語言與休閒環境的改變,唸歌曾一度消蹤匿跡,被貼上傳統呆板的印象。要讓唸歌的口頭藝術重新回到大眾的休閒視野,首要解決的困境便是打破刻板印象。2016年,國寶藝人楊秀卿、微笑唸歌團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團隊一起合作,拍攝〈唸啥咪歌〉MV,對於傳統的再演譯具有代表性。
〈唸啥咪歌〉以歌仔冊《哪咤鬧東海》的故事為主軸,進行聲音「影像化」的改編。MV以文字拼貼手法表現唸歌的即興表現能力,亦透過各種具跨時代意義的圖像,引起並獲得觀眾的共鳴。例如影片中形容戰況趨於混亂的時候,歌手扮演龍宮太子的角色,說到:「話一講煞,太子飛去半空中」一句時,畫面突然被放上「超人」的圖片,接著在後面關於龍珠的形容中,則被故意誤解為「宋七粒」與漫畫「七龍珠」。
透過無厘頭的連結方式,讓唸歌的傳統框架得以被打開,找到與現代接合的契機。透過口白混搭現代時事創造詼諧感、唱曲重回傳統故事軸線並扣合「鬧」的混亂風格,以及口白與唱曲二線對立且分工的方式,成功演繹一曲傳統唸歌《哪咤鬧東海》。此專輯更因此獲得2016年德國紅點最佳設計大獎,讓台灣的無形文化資產站上世界舞台。
除了以音樂影片進行唸歌視覺化的現代演譯以外,唸歌歌手的文化身分,亦被新媒體引用,進行影像敘事。例如,電影《血觀音》中,邀請楊秀卿老師以旁白詩人的角色出場,借用盲人歌手「詩人」與「智者」的特質,加上台灣講唱「勸世歌」的傳統,可以說是另一種唸歌傳統的再現身/聲。
台灣唸歌國寶級藝師 ─ 楊秀卿(1934-)
民族藝師楊秀卿,4歲因高燒而失明,7歲開始學習唸歌,12歲學藝有成,始行走江湖賣唱,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又到現今的台灣,走過賣藝走唱、唸歌賣藥、廣播錄音各個階段,楊秀卿的一生彷彿半部台灣唸歌歷史,並以獨創的「口白式歌仔」(邊說邊唱)名聞台灣。此新穎的唸歌表演在誕生後立時備受喜愛,吸引不少新的唸歌看客。
文化傳承上,弟子中不乏主動登門求藝的知識分子,顛覆以往只有家貧者才會學習唸歌的刻板印象。2009年時,楊秀卿與弟子儲見智、林恬安共組主打創新、打入年輕族群的「微笑唸歌團」,2010年成立「楊秀卿說唱藝術團」,完成其對傳統技藝的保存與傳承的心願,並積極展開傳藝工作,為保存說唱藝術文化而努力,2017年更擔任電影《血觀音》的旁白詩人演出。
楊秀卿一生因唸歌而獲獎無數──1989年獲教育部「民族藝術薪傳獎」、2007年獲第11屆「國家文藝獎」、2009年獲得「第1屆台北傳統藝術榮譽藝師」、接著被文建會(文化部前身)指定登錄為國家級無形文化資產──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成為大家俗稱的「人間國寶」。
一把月琴與車鼓 ─ 吳天羅(1931-2000)
吳天羅,人稱「天羅師」、「天羅伯」,生於雲林縣土庫鎮,生活時代正值民生凋蔽的日治末期。吳天羅身懷說唱技藝,曾走過江湖賣藥、跟過歌仔戲團學習丑角、學習台灣鄉土藝陣「車鼓陣」與「牛犁陣」亦曾與友人共組二人歌仔戲班──即所謂早期歌仔戲的雛形「落地掃」。
吳天羅的唸歌,故事多取材於日常生活與時事,如台灣921大地震時期創作《集集大地震歌》,關心台灣鄉土與百姓。代表作長篇敘事《蔣公抗日歌》(或稱《台灣歷史說唱》),自明末台灣的開發一路唱下來,描述日軍進佔土庫鎮時情形,及當時百姓的生活情景。
除唸歌藝術,吳天羅亦為車鼓陣的傳承人,其子吳現山接手其所創立的「旭陽車鼓陣」,以極具台灣本土氣息的車鼓表演,在廟會、婚喪喜慶等場合中演出。
吳天羅一生創作豐富──拿著一把獨創的「六角月琴」,搭上自己所編的歌曲,將江湖調發揮得淋漓盡致。2000年,吳天羅獲「民族藝術終身成就獎」,可見其對民族藝術之貢獻。
月琴、嗩吶、大廣弦,多種樂器與說唱的合奏 ─ 王玉川(1930-2016)
王玉川,出生於新竹市黑金町(現新竹市東區頂竹里),為台灣唸歌藝師,其所擅長的樂器十分豐富,不只有唸歌表演常見的月琴、大廣弦,更有嗩吶、殼仔弦、三弦、吉他等;唸歌中的說、唱、拉、彈在王玉川身上皆信手拈來。早年王玉川曾自言自己幼時對唸歌的印象即是台、日語混搭的歌曲,其改編之唸歌作品極具台灣鄉土特色。
電音說唱的獨特魅力──陳美珠(1937-2019)
說到陳美珠,必然提起她手中那把「電吉他」──打破傳統說唱使用月琴、大廣弦合奏的形式,雖然頗受爭議,但也成為說唱藝術的另類創新。陳美珠與師兄王玉川相同,早期皆以唸歌做為賣藥的廣告手段,後期二人成為唸歌搭檔。
師妹陳寶貴為陳美珠另一搭檔,二人有一錄唱電視節目「錦裙玉玲瓏」──此節目即是許效舜、澎恰恰在1999年所拍攝節目「鐵獅玉玲瓏」的模仿對象。2016年,陳美珠與陳寶貴這一對說唱搭檔,一同被新北市政府指定登錄為新北市「說唱傳統表演藝術保存者」。
微笑著說唱下去 ─ 微笑唸歌團
微笑唸歌團以推廣「唸歌藝術」為創團宗旨,致力於傳統唸歌文化與其他藝術形式的結合 ─ 不論是劇本新創或音樂改編等,做出許多跨界嘗試。不僅讓唸歌踏出台灣島嶼,更是用力立足本地,期許用「穩踏傳統、創新開展」的心,復興台灣唸歌文化。
其創團至今受邀參與各式演出,在國內對唸歌的推廣更是不遺餘力 ─ 2014年與跨國界M.i.樂團合作,以爵士樂呈現台灣唸歌的「勸世歌」。同(2014)年亦舉辦第一屆「台灣唸歌節」,持續舉辦至今(2020)已到第六屆。目標在於年度性、更大規模地向大家宣傳與推廣唸歌文化,邀請老藝人參加演出,唱出早期的生活記憶與民間故事;現場除了傳統藝術的演出外,亦有唸歌的文物特展供參與者參觀,使其透過視覺與聽覺的串連,更加完整的對唸歌產生經驗;2017年登上南台灣指標性的獨立音樂節「大港開唱」,呈現傳統技藝與搖滾之結合;2019年登上台灣文博會「演變舞台 Stage On the Move」,更受邀在2019總統府音樂會演出。其代表專輯《唸啥咪歌》獲德國紅點設計獎大獎。
找回府城古味 ─ 古意唸歌團
古意唸歌團時常在各地舉辦講唱會與小型演講,推廣台南當地的傳統音樂,也曾與西港東竹林牛犁歌陣合作,舉辦牛犁歌探館體驗活動,帶領大家在聲音中重返古早味的傳統府城。而羅士哲也曾開班授課,將唸歌團帶至華沙音樂學院等現代音樂空間,將台灣傳統音樂介紹給台灣囝仔。藝文界、音樂界的創作夥伴也與羅士哲一同合作,各有所長的創作者們聚在一起,在不同元素的激盪下產生更多創作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