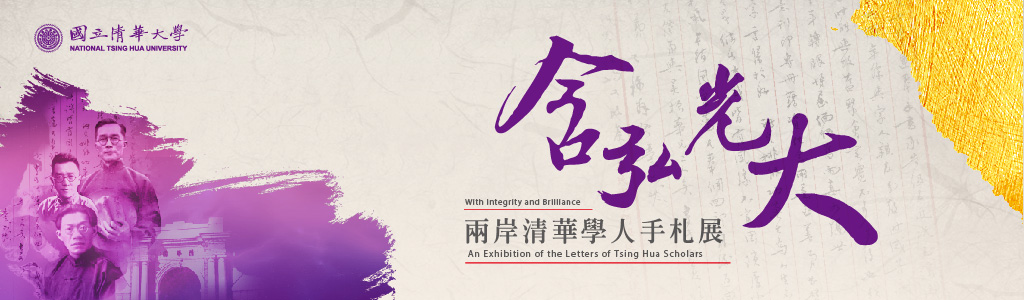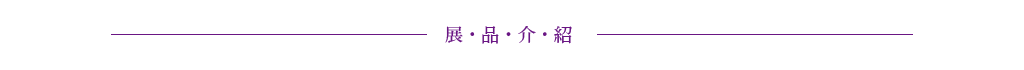
作者介紹 / 李遠哲

李遠哲(1936-),臺灣新竹市人。臺灣大學化學系學士、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1961級)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博士。李遠哲在攻讀博士期間對離子分子間的作用、分子散射的動力學產生研究興趣;取得學位後,李教授前往哈佛,在Dudley R. Herschbach教授指導下進行博士後研究,於1986年獲諾貝爾化學獎。除諾貝爾獎外,尚獲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日本學士院客員、宗座科學院院士等學術榮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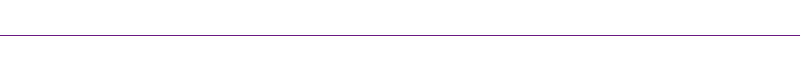
李遠哲/憶昭鼎兄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珍藏資料)
釋文/
憶昭鼎兄 李遠哲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晚上,我帶著幾分疲憊飛抵奧克蘭機場時已是十點十分。在濛濛細雨中到機場接我的錦麗也似乎格外沈默,回家路上我一直述說著這一星期來的所見所聞與旅途的感想,也照往例先繞道到加州大學的辦公辦室料理一些急待著我處理的一些事情,在一大堆傳真中看到了幾張昭鼎兄寄來有關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的中文信,在信紙的右上角寫著「星期五晚上再打電話給你聯絡討論」。回到家裡稍事休息之後,眼看著時鐘快到午夜十二點鐘,心想那該是昭鼎給我電話的時候了。忽然坐在對面的錦麗輕聲說道:「遠哲,我有一個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訴你,昭鼎兄今晨與世長辭了。」這句話,像雷電的衝擊,我頓時情不自禁地用手掩住臉,隨著兩道熱淚,墜入百丈深淵。他不該這麼早就走,也怎麼不先告聲別便悄悄地仙逝呢?他不是在等著有一天我也回去為台灣的科學與教育共同努力?我們怎麼沒有能好好保護他?無數的往事映入腦海。
一九五五年秋,我帶著無比的興奮走入台大之門後,首先認識的異鄉人便是張昭鼎、張隆鼎兩兄弟,從台南來的隆鼎與我同屆,是那年聯考丙組的狀元,高我們兩屆的昭鼎是化學系大三的學生,也許是那股不願同流合污的傻勁與對人類社會崇高的理想,我們便成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隆鼎、比我年長兩個月的堂兄遠輝與我便成為台大四年裡同寢室共同生活的難兄難弟。昭鼎、隆鼎在台大的日子完全由家教的收入維持,他們幼年失怙,母親把幼小的末雄讓楊家領養,把隆鼎留在身邊,剛初中畢業的昭鼎便隻身到台北開始獨立謀生的日子,幸運地在台大法學院覓得一個工友的職位,下班後晚上便在夜校唸高中。這一段餓體膚、磨心志的辛苦歲月,他從來沒向他的朋友們提起過,如果不是隆鼎告訴我他們兄弟過去的種種事,我是怎麼也想不到這位面帶笑容、堅定、和藹、善良的昭鼎,是當年曾經在領薪水的前幾天,因囊空如洗而好幾天餓著肚皮苦讀,也不願求助於人的志士。雖然他不願多談他自己,但是他卻常津津樂道他母親是台灣早期起義抗清的「鴨母王」朱一貴的後裔,他的血液裡確有那股接受新思潮、敢於反抗壓迫的勇氣。他的性格也有那像「鴨母」一樣的溫暖,與他非常接近,人便常以「鴨母」稱呼他。我門這樣稱呼他,他總會給我們會心一笑。
在我求學的生涯裡,昭鼎曾給我非常深遠的影響。他不但是一位值得學習的學長與深交的朋友,而且確也是我啟蒙的老師,是他指點了我為了要成為優秀的物理化學家,一定要在熱力學、量子力學、電磁學、統計力學打好根基,要成為一位實驗科學家也該學好電子學等事。還記得大一的暑假為了想與昭鼎一起學好熱力學,我曾經待在台大第八宿舍而沒有回家,我們找了一本Lewis and Randall熱力學的書,便興致勃勃地開始輪講。他很有耐性地講解一些我不懂的事。那暑假我們學了很多,但當我們碰到怎麼也不能了解的難題時,卻也找不到高人指點,幾位教授也只能告訴我們,我們還年輕,不必急於懂得這麼多,但是我們卻知道,如果不努力,歲月的增長並不會使我們更聰明。我大四時鄭華生老師指導我的學士論文,也多少是受了昭鼎的影響。他說服了我與其與一位成名的教授做老的課題,不如跟一位年輕的老師探討新的領域。把妻小留在新竹,在化學系當講師的鄭華生先生,除了週末回家團聚外,平日與我們日夜相處共同奮鬥的日子卻也是非常難忘的。
當我大學畢業邁入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時,昭鼎也在清大得了碩士學位,到日本東海村的「原子能研究所」進修。有一天,我接到他的一封信,說日本八個月的受訓便要結束,不久便能回來,希望我能到基隆碼頭接他。他信裡似乎有些不安地提到,他並不願意讓我放下學習與研究專程到基隆接他,但是他似乎有些擔心,他在日本時對政府批評的言論與廣泛的交友,是否會有人打小報告而遭受到上岸便被逮捕的下場。在高中時曾看過同班同學無辜被捕,幾年後被放行時已變得神經錯亂,我只希望這種事不會發生在這位我敬重的學長。
昭鼎回國後的兩年間,我們在清華大學的原子科學研究所,曾有過非常快樂的日子。北投石的化學結構所含天然放射線同位素的分析,與後來在葉錫鎔教授提議下利用台大醫學院鈷-60珈瑪射線(γray)做的有關高分子的放射交鏈研究,我們曾經廢寢忘食地共同埋頭苦幹過,在忙碌的日子裡,我們也曾偷閒遊山玩水、攀登高山。有一次昭鼎帶頭,連同比我高一班學物理的鄭文魁、陳瑞梧與我四人,從竹東乘坐林場的卡車到鹿場山爬山。爬了一天欣賞台灣中央山脈的美景後,我們便在接近山頂的林場招待所過夜。昭鼎對於陌生人總能一見如故,看到招呼我們的一位年輕站長,不但彬彬有禮地感謝他的幫忙,也稱讚他這麼年輕就能夠有這麼好的成就成為工作站的站長。那時我還取笑他,明明比那位站長年輕很多,卻如此「倚老賣老」。不過曾經刻苦奮鬥過來,經過磨練與考驗的昭鼎,在年輕活潑的臉孔上,總會浮現出他那特有的信心與老成。那天晚上我們促膝長談,談了不少我們的研究與將來,但無論怎麼樣,總不能說服端梧爬山是件有意義的事,爬不到一半便開始埋怨的他,總想不通我們為什麼爬到山上來,他說山上又沒有我們要找的人,只是浪費時間。於是第二天一早便獨自下山回去了。我與昭鼎、文魁兩位在山上多留了兩天,也登高爬低地走了不少地方。第三天傍晚,林務局有人追過來說新竹警察局來電話說,電信局有我從美國寄來的電報,須我下山領取,那時電報的消息總不是吉利的。他們兩位替我擔心,難道在美國的遠川兄有什麼急事。趕下山來才知道那不過是芝加哥大學通知我要給我優厚的獎學金,希望我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一九六二年我與錦麗訂婚後,便到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昭鼎兄也得獎學金到德國留學。這一別便有整整十年我們沒有再見面,直到一九七二年清大徐賢修校長邀我到清大當客座教授才又看到已成家且有三位子女的他。年輕的張昭鼎教授在清華確是位最具魅力的老師,他開明民主的作風,對學術的熱忱與對學生的關懷,很快地便成為學生們崇拜的偶像。那時在清華大學很多學生常自豪地向人炫耀張昭鼎是他們的老師。張昭鼎的學生們與別人不一樣的是,他們除了對學問探求努力不懈外,他們也關懷人群社稷,懷抱著寬廣的胸懷,願為社會的進步貢獻心血。我非常敬佩昭鼎兄,這麼多年來能夠一直堅持他的理想而努力奮鬥,也慶幸清華大學的學生們能有一位這麼好的教授。客座期滿,回芝加哥大學繼續我的教職後,我們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那一陣子,昭鼎為了充實清大化學系圖書館,努力籌募化學圖書基金,也督促我向美國年長的系友發動捐款。也許這一群年長的清大化學系的系友,都受過昭鼎兄無私的薰陶,捐款的踴躍令人感動。不過我沒想到十年後的一九八二年開始,昭鼎兄與我又開始另一形式的更密切的合作。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我隨美國科學院化學代表團到中國大陸訪問,回來幾個月後,我在學校餐廳見到了從河邊加州大學來訪問的浦大邦教授,我們彼此聽過名字,但這還是首次見面。他問了些我訪問大陸的感想,也深入討論了些有關台灣科技發展的種種事,那次與大邦兄的見面是很令人興奮的。我們找到了一個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希望我們能夠為台灣科學的發展奉獻心血。非常能幹而神通廣大的浦大邦教授,便著手籌組了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召開的「原子與分子科學研討會」。這個非常成功的會吸引了海內外許多出色的科學家,也為以後中研院的「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與「行政院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的催生發生了些作用。
一九八二年中研院的院士會裡通過了「原子與分子科學籌備處」的設立後,大家便推舉了張昭鼎來擔任籌備處的主任,我也接受了原子與分子籌備處的諮詢委員會主席任務。剛開始的一段日子百廢待舉,為了建立籌備處與大樓的籌建,有那麼多瑣碎事。他一方面在清大教書,另一方面更為原子所的設立到處奔波。設在台大校園內的原分所,事情是更為複雜了些,與台大校規會的溝通、營建處的大樓規劃與找建築師設計、比圖等不知費了他多少心血。雖然我常回國幫忙,但總的說來,原分所的開創,尤其是大樓的建案,完全歸功於昭鼎的努力。
我還記得有一天,他帶著笑容向我走近,看他的表情我知道一定是有什麼對原分所有利的消息。他說:「遠哲,雖然諮詢委員是不支薪的,但是諮詢委員會的主席每個月有……。」我沒等他說完便說:「你刻個我的圖章,留在辦公室,每月領了錢後,就給原分所彈性使用。」講了這句話,我們倆便哈哈大笑。我們都高興他這則消息給原分所帶來了小小的額外收入。諮詢委員之一的南加州大學的張圖南教授,常覺得奇怪像昭鼎兄那麼慷慨的人常花自己的錢請朋友,但對原分所的開支卻都一直斤斤計較,能省則省。不過我知道這只不過是他高尚人格的局部表現。他能夠、也希望別人也能「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當韓忠謨教授是中研院總幹事的時候,也曾非常讚許昭鼎兄,他覺得我們請他當籌備處主任,確是最適當的人選。他雖不是辦事務的人,但是在海外的我們是能夠完全信賴他,知道他會把該做的事情做得很好。
這十年來,為了原分所的發展,我們共同努力過,原分所舉辦的許多研討會、國際會議,常使我們一起密切策畫,並相聚在一起。這幾年來隨著我返台次數的增加,與對台灣科學與教育方面工作領域的擴大,便也添增了他不少負擔。幾乎我在台灣所有的事情都經過他聯繫,他像親兄弟一樣地照顧我、保護我,如果沒有他善意地指點迷津,我那過分相信別人的習性,怕要承受不少傷害。
今年三月下旬,我回國以前便聽到他氣喘又發作而住在台大醫院裡,我打電話慰問了他,但他一直堅持他已好了,沒事了,便也討論了許多有關原分所與其他的一些事。我回國後,他好幾次從醫院請假出來參加一些活動。他說是醫生允許,沒問題的。我心裡覺得非常不安,但看他身體十分硬朗,便也相信只要把氣喘鎮住了,不會有什麼事。怎麼知道這次的會面,竟是最後的一次。
他真的就這樣默默地走了。他背負著台灣科技界、教育界朋友們無限的希望, 是我們心目中的英豪,他不該這麼早就離開我們的。這幾年來他一直勸我早日回台工作,總該也是回國工作的時候了。我也答應了他,我將盡早回來幫他,一起為台灣的科學與教育共同努力。我們不是要在今後五年內把原分所的科學研究工作趕超世界水準嗎?我們不是要同何壽川夫婦、劉源俊教授予關心中小學教育的人,經過(紙本結束)
內容說明/
敘述甫結束長途行程返家後,妻子吳錦麗告知好友張昭鼎去世的消息,悲痛莫名,難忘在台大求學期間與張昭鼎相識結為好友,一起追求學問的點滴往事。當年的張昭鼎不但是值得學習的學長也是啟蒙的老師,指點他要成為優秀的物理化學家,必須要在熱力學、量子力學、電磁學、統計學等領域打好基礎,還建議他與其找成名的教授研究老課題,不如找一位年青的老師探討新的領域,讓他難忘與當時的化學系講師鄭華生先生共同奮鬥的一段時間。
當他在清大原子科學研究所就讀時,張昭鼎在清大已經拿到碩士學位遠赴日本東海村的原子能研究所進修,有一天他接到張昭鼎來信說,受訓即將結束即將返台,希望李遠哲去基隆碼頭接他。因為張昭鼎擔心自己在日本期間可能因批評政府以及廣泛交友被打小報告,以致上岸便被捕。李遠哲以高中曾見過同班同學無辜被捕,幾年後被放行時已經變得錯亂,不希望這種事再度發生。
他到柏克萊攻讀博士學位後,張昭鼎也到德國深造,兩人十年間未曾相見,直到1972年他應邀回到清大擔任客座教授才再度見面,此時張昭鼎以其開明作風、學術熱忱、關懷學生,備受學生們的愛戴,他也受託為清大化學系的圖書館向系友募款。十年後兩人又一起籌備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擔任籌備處主任的張昭鼎為此奔波付出許多心力,「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一如他一向的人格表現。這段期間李遠哲多次返台,參與台灣科學與教育的領域也逐漸擴大,所有事情都由張昭鼎居中聯繫,張昭鼎像親兄弟一樣地照顧、保護李遠哲,如果沒有張昭鼎善意地指點迷津,李遠哲自認以自己相信別人的習性,怕要承受不少傷害。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編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