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走詩到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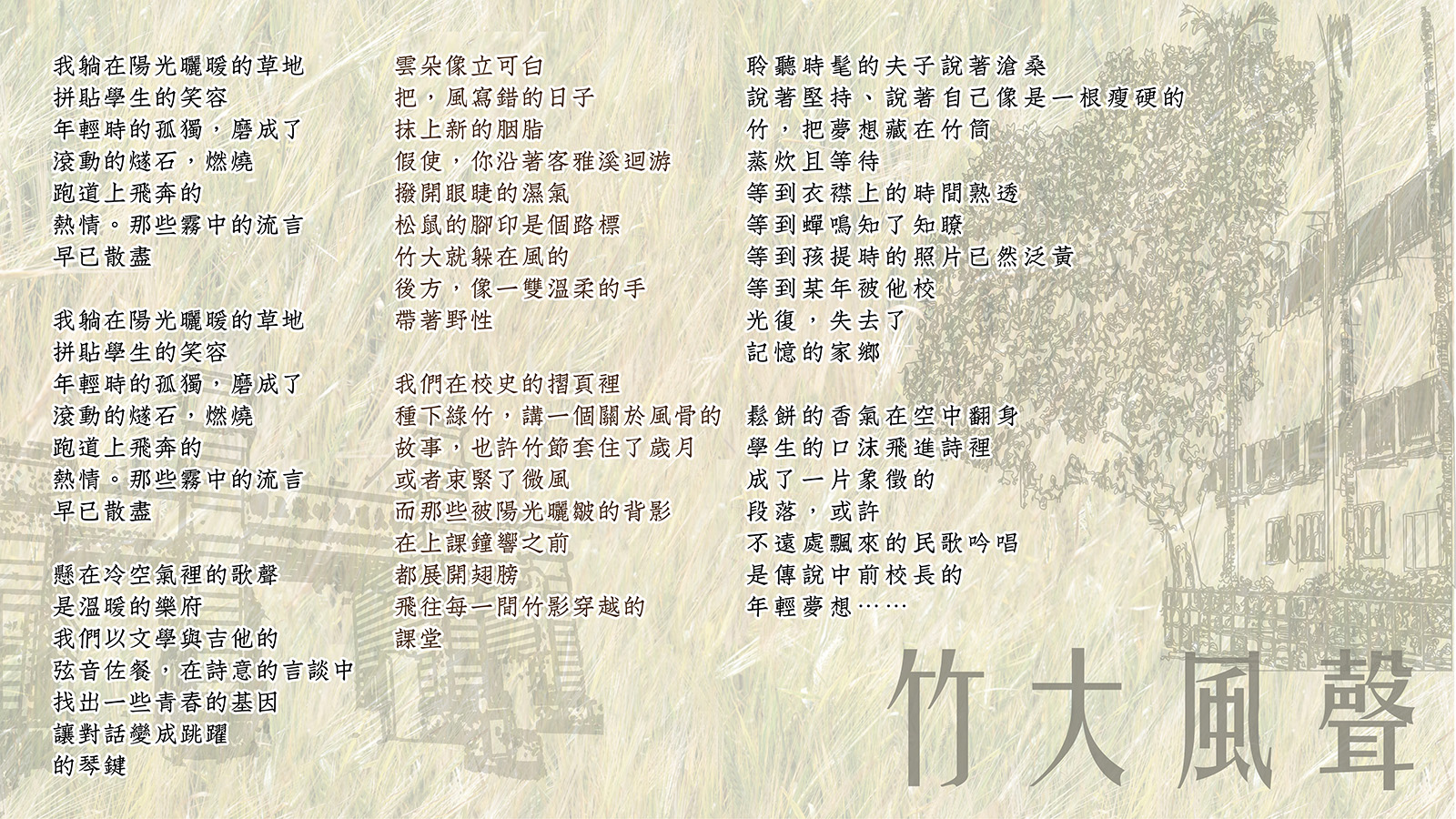

暫厝的海景——寫在正濱漁港
我們暫厝彩色的海屋,於和平島南方的港
漁船是沒有秒針的時鐘,快門的背影在碼頭
漂浮,我把急促留給遊人的街,飢餓感寄杯廟口
以緩慢的詩句撿起狗吠,在濱海的堤岸找到
反光的露滴,從窗臺推出一扇模糊的海景
陽光溶解港的哀傷,我卻是海做的琉璃
為了向阿根納造船廠頂禮,海鳥在時間的
波面,以波浪換季,我跌進中年的晚景
捕撈遠航的青春,天色如詩,暴雨在遠方
打卡,沈默的階梯,彷彿我駐足的星球
柳樹像是船桅,年輪是舵,我們為了雨季
展開絕版的旅程,岬角與海岸都愛上
望海的日子,三角戀情的敘事裡,我們
細數著階梯,或許誰也不該在晨間
夢遊,在午後擔憂天空的陰鬱
慰靈碑前,磯釣的老者以釣竿拉起晚來的
光陰,碼頭的海風有些黏膩,港灣有如
銀河圍起的城,食材們把海洋帶上
瓷盤,我聽見水聲,晚餐變成一種書藝
舌尖如魚,於齒間擺動尾鰭……


編年台北・我的一九七四
這一年,台北是一個寧靜陰鬱的城,我、林志玲與謝金燕在該年出生。
我把兩棲的意象
寫在外牆
虛度感冒後的晨光
那記不得的一九七四
枯燥的日常
剖腹取出了一箇
提早壞掉的
舊時光
一九七四的台北
除了斷交,就是拓寬許多交叉的
街,世界突然安靜
除了山裡的蟾蜍奔火
與總統的攝護腺炎
高爾夫球俱樂部
變成青年公園
而這年難得的寧靜
預言了明年的
暴雨
婉轉的年代
我們聽見暗殺的疑義
熬夜被獨立的文法
註釋,而另一邊號稱家鄉的
秋海棠葉
正在批林批孔
四人成了
黑幫
我們需要炸雞
在這個頂呱呱的一九七四
姊姊與志玲
於南北先後降臨
但有些殉難墜毀的生平
只剩下碑誌的
窟窿等人
認領
據說那年,我是憤怒的種子
從母親的腹部萌芽
化簡為繁
幾十年後以一首首假借的詩
向你們轉注失控
的青史




誰說,書屋只能汲古:詩記林本源家族
三合吉日
宜祭祀、上樑、修造、動土
忌嫁娶、安葬、作灶
誰說,書屋只能汲古
我們歇息,在水池旁想像漳泉械鬥
想像自己在雷鳴的深夜
穿越邊界,勘察大嵙崁的暮色
道光年間的農民曆
墨漬斜曲,像是暴雨的河道
於是,你打算佈防孤獨的高牆
裝潢古城的卑微,以弼益
二字,撐起家族的天
我們曲折前行,想踏進你打理的
院落,複習方志記載的激情
與新生的暮色,那應是咸豐元年
城牆剛經歷了一次整形
手術像是祭典,方鑑齋的戲臺上
咿呀的胡琴把式隨風聲遠颺
而香玉簃裡盛開的花語
依舊如此輕盈透明
翹起燕尾的屋簷守護著
宅邸幸福的倒影
風隨機吹開光緒年的折角
泛黃的標誌彷彿你
獨自垂釣於水榭
在月波裡悟道:定與靜
兩個交錯的菱形
像方正的心
誰說,書屋只能汲古
我們的座標移往池北的假山
看見長衫搖曳,而拗口的
方志,變成了池底
一隻隻後現代的
鯉魚⋯⋯


走詩桃園——鐵塔的自語
——「醜又不是我的錯。」
我竟像是惡靈
夜半的唱腔驚醒
山巒的睡意,四散的
霓虹,驅逐螢火
與星空的
交誼
遙望遠方的高跟鞋姊妹
藍色的光暈
增加近視的深度
別再罵我東施
人生總是
不得已
我知道巴陵不是巴黎
但爹娘卻強迫
給我一副
發亮的
身體
還說我是祖靈的眼睛。

兩葉的相守~北埔寶記茶莊紀行
膨脹的風掠過彎道
我們循著茶菁的氣味
收成鎮日的倦意
而琥珀色的夕陽停在茶海
守候愛情的
蜜香
一心可以一葉,也可以變成
兩葉的相守,小綠葉蟬
咬緊青心大冇的茶樹
留下了耐泡的相思
我的承諾重度
發酵
從芒種行過大暑
回甘的平常
日照充足,我們帶回盛產的
人情,與陳年的春蒔
泡一壺夜色
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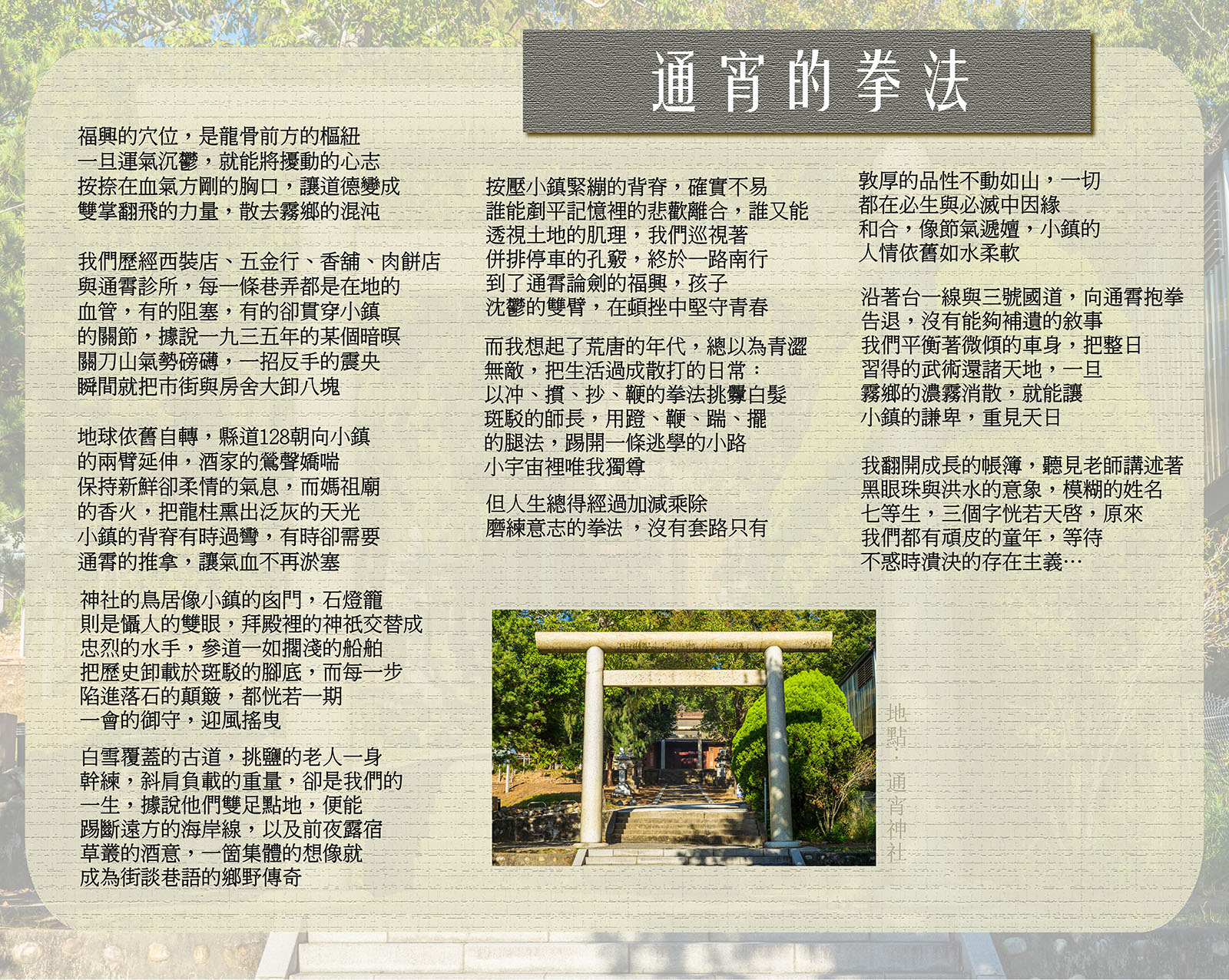
逢甲八景·人言大樓
人言誰說可畏,我們站在高樓
想起一段清談的日子
攜著新買的詩集
流浪的雲朵
是塔頂的雨棚
人言並不可畏,指向天空的
高樓,載著搖晃的夢境
穿越逆向的日常
一粒砂、一塊磚、一寸鐵
都背負青春的
腳掌印
人言的確可畏,當我們遺失
距離,就得登樓遠眺
放課鐘聲有如微風
吹向課室的初戀
與階梯
進入埋著敦煌的洞窟
我們拎起一杯咖啡,與象形的
篆體,一路從絲路走來
上課也是一場
戰爭史
人言何以可畏,十四層的高樓
不曾凋謝,我們信仰自由
也堅持掀起一把風波
向遠方的夢想
仰頭致敬
而廣場裡
一群文藝復興的孩子
排演著新版的哈姆雷特
依舊很文青


走詩磺溪—印象小西巷
我在古佛前合掌
想像道光二十八年的震央
把格局搖出了破口
過水廊的金爐裡
香火堆成了記憶的
聚落
我們穿過巷弄,時間從腳底倒流
仿佛看見竹寮草廟的一生:
起厝、擴地、焚毀、重建
據說廟口對著北門
土地公一搖身
竟鍊成包租公的
不壞金身
那就繼續前行
成衣巷、老銀行、大酒家的傳奇
都已荒頹,針線與拉鍊的
愛情,早就解散
接線生的白髮比光陰還長
狂歡的春秋不再紅葉
只剩下文創的
咖啡香
至於那間老店與對面的阿彰
把肉圓浸成油膩的觀光
傳了幾代的貓鼠麵
糯米炸的命名學
仍是饕客最好奇的
舊意象
而北門口漲價的
日常,爌肉飯的豆油香
都讓我們的味蕾
與無解的疑惑
感到慌張
但戲偶的眼神堅定
以鋸木屑、太白粉與水的三角
函數,換算出青春
的距離,與老人家的
童年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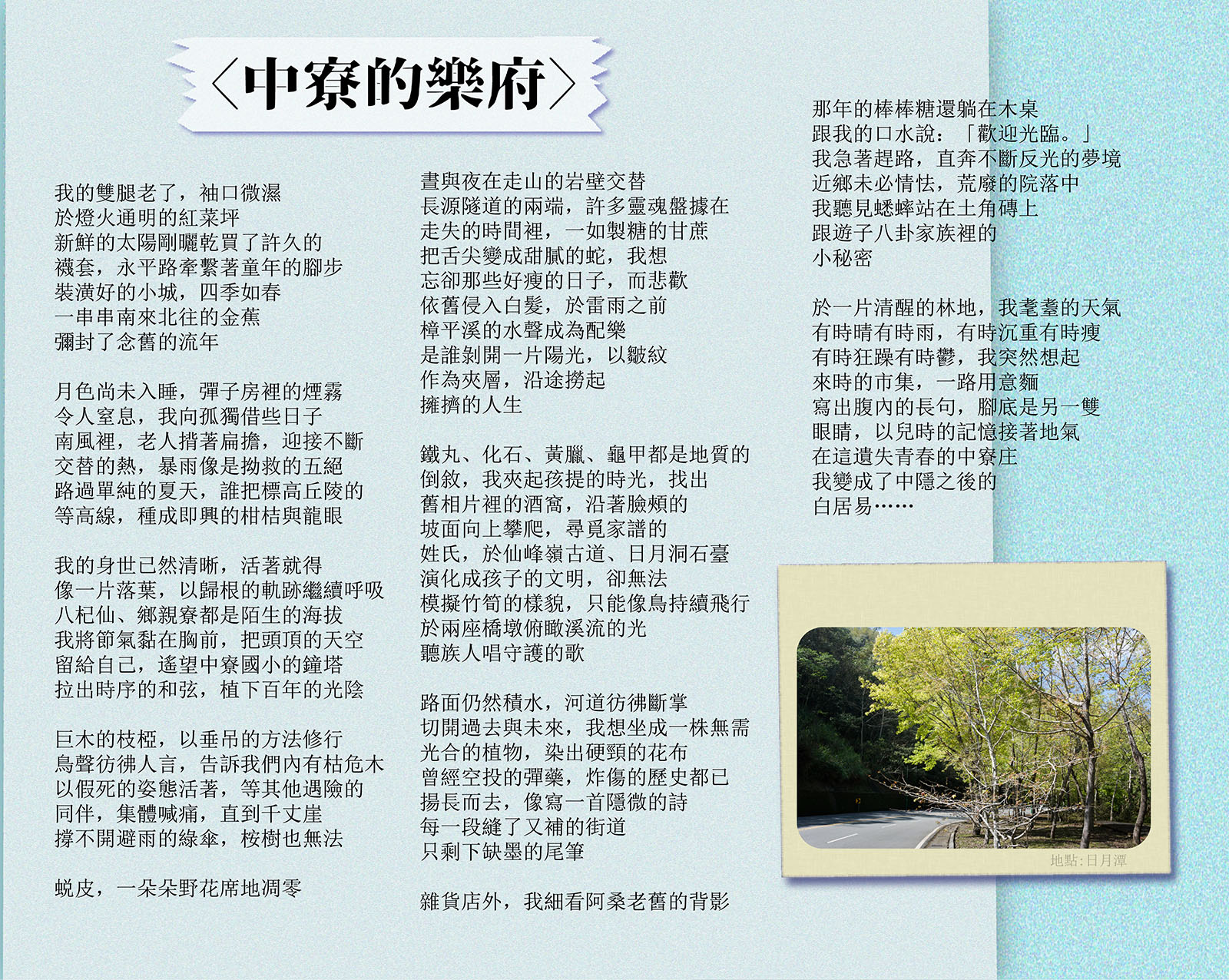
他里霧的雲彩—記斗南高中演講與校長、老師們的熱情
我從簡約的幾何線條裡
找一條慢活的路徑
於純粹的午後,純粹的暖意
被踏出一道彈性的
軌跡,一公里的時空步道
穿越了日治與
有機的學堂
你們把性情走成開朗的步履
於言教、身教、制教、境教的
畫框,我聽見樂活的夢想
站前的四斜屋頂
被點染出曲折細膩的
簷廊
故事總是這樣開始的
關於文青的哲學
都需要攀折
一些精緻的悲歡與離合
我匆匆的來
揮一揮手,背包裡滿載著
他里霧的
歡笑和雲彩

悲歡八掌溪
我們翻開方志,行旅到了康熙年間
彌陀寺旁的渡口,八獎溪水
沖散人們湍急的一日,那些無法
載運的青春,以每秒一千八百
立方公尺的速率,向出海口
索討沿岸困居的人生
我們自南門出城,從田仔、草地尾
向諸羅山大圳橋開拔,據說溪畔
南方是蓮花圍繞的白河,東南
就是那一座壯美的阿里山
「要打這過,請繳索費。」
我們沒錢,只得穿越道光二十七年
那一頁,碑文記載的義渡紀念
讓窮人產生遠望的想像
一切翻轉的可能,都以渡頭
作為圓心,陀螺的小世界
轉出一圈圈熱鬧的街市
而鐵線橋、白鷺橋到忠義橋的離合
悲歡,從大正年間一路行來
就是數十個春秋,八奬溪也在
唇齒的咬合中,變了口音*
古蹟園區裡的土地公與義民塔
依然護持者迷航的魚群
那年的吳鳳橋下游
被當作螻蟻的四名工友緊緊依偎
而我們都躺在無能為力的
沙發裡,看見他們被
暴水沖走的最後
一滴淚
*八掌溪原名八奬溪


不哭~寫在台南震災之後
我不想與震央一樣濫情
把詩句寫成拭淚的
面紙,但那些倒塌的樓層
掩埋了恭喜的
鞭炮聲
我們說好不哭
在另一個南方踩街,卻踩向
家園的前線
慌亂的冷鋒就要過境
遺失的除夕等待
救援
我們無法不哭
土石堆裡的心跳聲逐漸
微弱,地表
已翻了好幾箇身
過一夜,年頭就白髮了⋯⋯

走詩高雄・蕉城的光陰
不穩定的氣流,沿著時光的機翼被雲朵
吞沒,我們把日常拋在異地,每段
平移的象限,讓故鄉變成他鄉
蕃薯寮的敘事不必置換語感
不必調動步履的寬幅,仍得在邊界
拉起歷史的錨,從施里莊入境
以免被扣留剩下的光陰
「北九份仔,南旗山」
摺頁停在大正九年,改名換姓的時代
亞熱帶的旗尾山,變成不必驗身的
出境點,微笑的弧度從樹上昂揚
我們從國道10號向東,尋找街屋
以及石拱圈、亭仔腳,除非排隊
或者逗留,沒有入境的方法
我們沿路遞換視角,從台3線右轉
於旗尾橋,逐漸偏移中年的景框
一旦拉近想像的潮汐,就能澆熄昨夜
床笫的火苗,老人的回憶就在前方
風華絕代的糖廠換個方位,就能偷窺
天外天的酒家菜,與阮寶治的手勢
柯水發的憤恨,一同流亡
「三腳步一茶室,五腳步一酒家。」
我們跨過香蕉的盛年,歷史更加泛黃
時間是青苔的工匠,六十年代的靜養軒
繼續暗室的翻滾,樂春園、新安樂
與水月宮,彷彿嫩綠的舞踊,環抱著
蕉農的汗衫,哼唱不熟的情歌舊調
於流年的審查,變成碑面的天光
在蕉城的前世,我們以腳印蓋上郵戳
旗甲、旗南、旗山與旗尾,黃色
或綠色的微笑,弧度像是弦月
胭脂的香氣,把過去妝點成繁華的
市集,我們的雙唇有如蝴蝶飛進了方志
也飛過了媽祖廟前的香爐
蕉城的今生,卻從戰前的老街
沿路文創到底
而巴洛克的一生
證明了黃色的意象是一種
慶典、競賽,一種與記憶的搏鬥
而船艙床場的光合作用
似瘟疫蔓延
幾棵蕉樹靜靜凝視有無的山色
於新開的茶廊前,我們的臉頰變成
落葉,被風吹出時光的波瀾
我們仍從施里莊出境
背包早已裝滿一整袋的
金蕉⋯⋯



珊瑚賦—寫在後壁湖
固著或是游離,於一個逐漸混濁的
海域,蕈珊瑚是夜行性動物
沒有人跡的遺囑,逐漸在夜色中
傾覆,體腔裡,想要浣衣的魚
在海底與水草相思,體腔外
觸手回到了那年的白堊紀
如果海洋是晶瑩的廣場,苦難的
沈積物,都在趕路,無法剔透
晶瑩,洋流把光影拖出紅線
抄一條通往水面的近路
太陽都留在夢裡,突起的
邊緣,像是光陰的指尖
沒有人以敗絮為榮
指型軟珊瑚的信仰仍比
一首詩難懂
五公尺的水深,閏過的月份
已經迴光,中年的蜃樓
尚未污染卻已被水草掩映
柳珊瑚像是深海的幽魂
迷人的軀殼裡,眼淚從骨針
湧出,我們潛進深秋的夢
佔領一塊岩石,以觸手
祈禱,他們說負心的
不是魚,而是水草
海面總是出現幾道皺痕
藤柳與黑柳涇渭分明,波紋之前
白晝依靠夜色,枯樹以外
只剩落葉叛亂的風波,從深海
開始革命,如果水草變成
繩結,海扇的記憶
就會清晰,浩劫
也不斷重生
我們蒼茫遼闊的藍色海洋
除了病,一無所有
如果海是藍色的鐵窗
珊瑚的故鄉都挨著水草
變成戀人敲開的
鐘響,有些凋零來自傷痕
有些來自於你⋯⋯


寫給台東的戀人絮語
我把童年藏在鹿野的鳥居,你說關山
站前的古厝,瓦房剝落了一段牡丹亭
越過馬武窟溪的東河橋,就更接近天堂
或許是風撿起了海岸山脈的落石,祈求降靈
喚醒先民北移的記憶,而溪口的河階逐漸抒情
雨聲把族人狩獵的迴音封印,變成聚落
變成月色被祖靈捏碎後,反光的遺址
中央山脈不需要條碼,不需要被商販訂價
而石頭與糯米戀愛了,麻糬成為日常的標記
時間如水聚積,釀成有點酒意的歷史
這是通往幸福的醫方,信仰是秘密的調配
我們把誓言悄悄丟給神社的靈獸
讓陽石與陰石的敘事,把寂寞交給
碑上的忠魂,以山泉洗滌夢境
我停在樟樹環繞的瑞豐,以古典的語彙
把詩句打磨成一把鑰匙,潮汐的吻痕
變成浮雕,遠方的官舍已文藝復興
預言並非遺址,童年還刻印在挑高的
鳥居、古厝的瓦房,以及秘密的古井


造型花蓮—壺穴的修辭
青春是一道峽谷,時間
是隧道的出口,我彷彿看見
腦中流動的瀑布
沿著破損的裂縫滲入
那堅固的記憶地表,或許
碎石墜落,或許雨聲
磅礡,我狼狽不堪的生命
在岩壁邊緣,終將開闊
沿著立霧溪回溯
消波石像是一群堅定的聚落
他們說:「玄武岩經過變質,
就成為綠色的塊狀結晶。」
而我非原岩
只是夾岸的覆瓦,在曲流的
沉積中
向河階致敬
溪水有如時間
悄悄打磨岩壁的桀驁不馴
鵝卵石則是記憶的
聚合,在溪流發育的日子裡
留下頑劣的痕跡
而壺穴的修辭
既非引用,亦不是象徵
那濺起的水花,在溪谷的
回聲,是鐵道與山脈
共謀的一次轉品
沿著立霧溪順流
風化的岩石往東遷徙
像築巢的燕子
你說:「在盛開的水樹下
沒有人是異鄉客」(註)
(註)此為陳黎〈在白楊瀑布〉一詩之末兩句。


潑墨宜蘭─湯圍溝紀行
我們的雙腳像魚
在溫泉裡
咬著彼此的呼吸的
鰓,而暖流
從指尖
掠過
一杯綠藻啤酒
我們聞到了海洋的
氣味,這一路自東南
潑向西北的墨漬
抽象出了
森林,以及梭羅筆下的
瓦登湖濱
我們終於決定
高速返家,把山水
裝進行李箱
貼上相戀的標籤
與林場裡的漂流木約定
下一季進行面試
以足跡做為
信物
而我們不會離群
卻仍想索居...

祖靈回憶錄

戰地的快遞~詩致金門
在步道,我聽見戰地的鐘響
含著糖果的風獅爺
在鏡頭抓下的風景裡
變幻各種姿態
砲戰下躲藏的戀人們
牽手,就簽下
一輩子的
信任,而後於一杯粉紅
的調酒,將高粱作為
信物,快遞至
風城的課室
還有聽覺裡的節奏
收錄了戰地裡的
轟炸、槍響、阿嬤唸歌與風聲
我們彷彿進入坑道
展開想像的敘事
那一個個風鈴般的御守
飄在一道道懷舊的
菜餚以外,召喚祖靈
組裝一幅新的
拼圖
謝謝你們攜來外島的風景
以各自的絮語,展開
視野,而繪本裡的
夢境提醒我們
別忘記兒時
擁有的
和平


